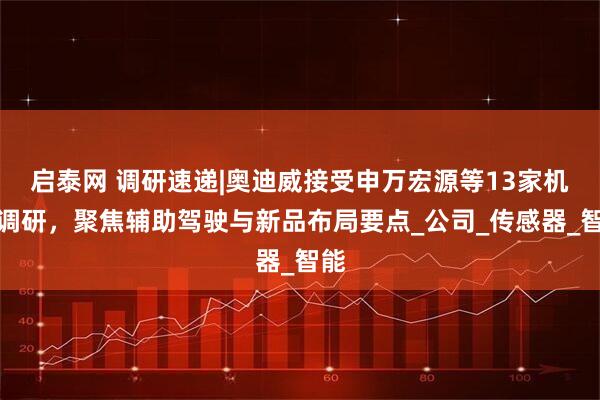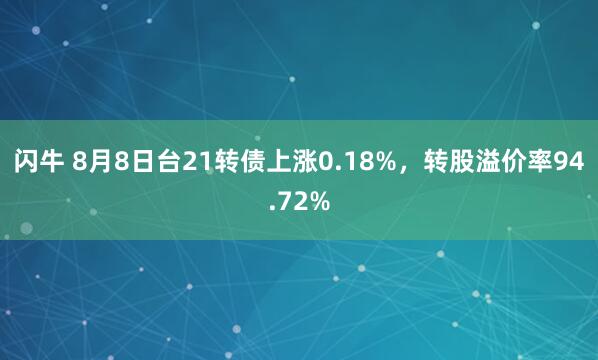【1945年8月15日夜,五台山】“总司令,老乡问咱还能不能留下来种地?”警卫员悄声询问。聂荣臻放下刚收到的日本投降电报泽巨配资,只淡淡回了一句:“咱们的根早就扎下了。”

胜利消息传来时,晋察冀军区已经拥有三十二万武装力量,分布在燕赵大地的沟沟岔岔。八年前,这里只有三千来人、两部电话、一部破电台。很多人惊叹这块根据地的扩张速度,却少有人记得它是怎样熬过最艰难那段日子。
时间回拨到1937年11月。卢沟桥炮火尚未散尽,中央一纸命令把115师一劈两半:林彪率主力南下作战,聂荣臻留在五台山。师里精锐几乎都跟着林彪走了,聂荣臻得到的不过一个独立团外加一些欠编营连。三千人,要在敌后腹地闹出一块根据地,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。
更棘手的是干部缺口。周建屏、杨得志、李天佑、韩先楚……这些能攻善守的悍将统统随主力而去泽巨配资,聂荣臻身边只剩“三个半”:周建屏、杨成武、陈正湘,再加“半个”黄永胜。面对如此窘境,聂荣臻没有争,没有吵,他只是把随营干部学校死死攥在手里。

干部学校的课堂极简:三个月一期,方针政策、土改要领、伏击战术轮番上阵,目的就一个——让每个参训者都能带兵打仗、能和老百姓说得上话。三个月后,这批“速成排长”被撒向各县。有人觉得培训浅尝辄止,可事实证明,一个能听懂命令的排长,往往比空头座谈重要十倍。
与此同时,聂荣臻启动“滚雪球”策略。工作队、侦察班、宣传小分队统统分散下去,任务分三项:拉壮丁、分田地、攀关系。风险非常大,一旦日军合围,单薄分队极易被各个击破。可如果死守五台山,三千人同样会被慢慢耗尽。聂荣臻赌了一把——把危险换成发展空间。
赌注很快见效。1938年春泽巨配资,吕正操率2400名东北军抵达冀中,部队装备完整却缺乏方向。聂荣臻立刻派去了数十名连排干部,以部队混编、政治动员的方式逐步改造。半年后,这支队伍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,番号改为“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”。不到一年,兵力翻了一番,还带来了16门山炮,这在当时简直是雪中送炭。

就在根据地蒸蒸日上之际,厄运扑面而来。1938年6月,周建屏因积劳成疾病逝。聂荣臻赶到新坟前,久久无语。周建屏是他手里为数不多的纯军事干将,这一走,晋察冀在指挥层面再少一道顶梁柱。悲痛归悲痛,战事却不肯等待。短短两个月后,八路军第四纵队在冀东拉起十万起义队伍,却因组织不及、后续乏力而溃散。事后检讨,缺少一位镇得住场子的主将,是最大教训。
更加严峻的考验来自1941年秋天。冈村宁次上任华北方面军司令,发动“治安强化运动”,集结七万兵力欲一口吞掉晋察冀。聂荣臻果断令各分区化整为零,自身留在阜平吸敌火力。不久日机频频掠空投弹,原来敌军已用无线测向锁定电台。聂荣臻让侦察科长罗文坊带电台向相反方向疾走,主动暴露,引来敌机狂轰。小分队被围数日,终依熟悉地形突出重围,而聂荣臻得以率大批机关人员安全转移。事后统计,如果指挥机关当时被一锅端,晋察冀的组织体系将至少瘫痪半年。

军事干部奇缺的问题,聂荣臻始终没有彻底解决,却用“量”与“机制”把缺口压到最低。到1943年,军区已形成连以上指挥员本地化、骨干轮训常态化的模式。部队虽不是处处高手,却层层有人顶得住,这正是根据地能挺过最冷风口的原因。
有意思的是,外界常把聂荣臻描绘成“技术元帅”,似乎他最擅长的是雷达、导弹。事实上,晋察冀时期的他,每天忙的都是征兵、种麦子、拆地雷这种最基层的琐事。正因如此,他对“兵从哪来”“粮怎么上”这些看似后勤的老大难问题格外敏感,后来主管国防科研,也始终强调“人才体系”四个字。

1945年,子弹声还未完全停息,晋察冀军区已开始制订向东北进军的编组方案。八年苦干,将三千人磨成三十二万,这份家底,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一支活水。林彪曾笑称,“要不是聂总管后院,咱前线也打不这么顺”。一句戏言,却点透了晋察冀的分量。
聂荣臻把电报放入口袋,面对夜色里期盼的目光,只留下四个字:“老办法干。”那意思再清楚不过——干部先行,武装自生。八年如一日的方法,依旧适用。
翔云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