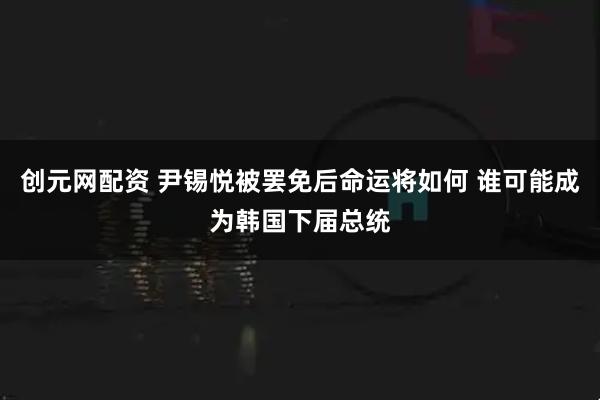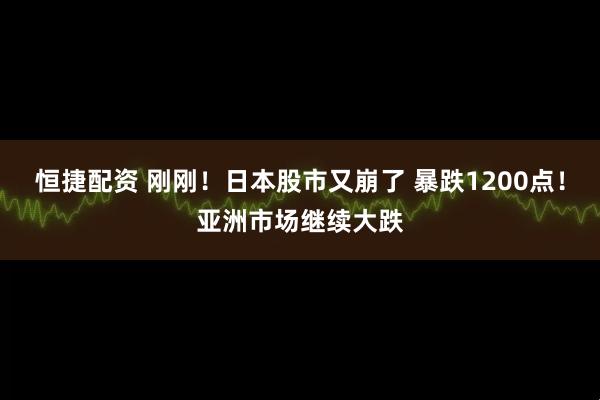“1977年12月的一个早晨,卢大爷,公社找您,有急事。”屋外的喊声冲破冬雾钻进院子星迈网,卢定义应声放下半碗苕粥,心口咚咚直跳。对他来说,“公社”两个字意味着审查、整顿、没完没了的口供,他想不出自己又犯了哪条条款。

步行去镇上的十里山路,他一直在琢磨:是不是去年分口粮时写错了数字?又或者生产队那头牛闹病被扣在自己账上?越想越乱,脚步却没敢停。到了办公楼,一位戴军帽的中年人把他迎进屋,语气和气得让人发毛:“辛苦您跑一趟,我们在找一位叫卢德铭的烈士亲属,您可认识?”
“卢德铭?”老人愣住,这名字在族谱里排在末尾,十几岁就外出,已是陈年旧事。中年人掏出一张旧黑白合影,照片边角驳落,墨迹却清晰:组织科员卢德铭,继雄,四川直宾双市铺邮局转。卢定义眯起眼,细看片中最右端那抹挺拔身影,猛地站起:“是幺叔!真真是他!”
调查组的三个人相互点头星迈网,松了口气。事情还得倒回十多年前:1965年春,毛主席重返井冈山。黄洋界浓雾里,他忽然低声问:“卢德铭找到了吗?”随行的张平化听得真切,却苦于无从下手。那时,关于卢德铭只剩姓名、牺牲地点,其余一片空白。

时间一晃到了1977年,井冈山根据地筹备五十周年纪念。张平化已在中宣部任职,再次强调:“卢德铭一定要列入英烈展。”江西方面临时组建调查组,可连张像片都拿不出来,展什么?目标因此锁定:先找影像,再寻亲属,补全事迹。
摸排从井冈山开始。调查员走访芦溪、萍乡、株洲,寻到韩浚、何长工、赖毅等老同志口述,才确认卢德铭早年就读黄埔。黄埔档案分散各地,于是调查组进京又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,与成堆卷宗打交道。翻到第十九册二期同学录时,陈明训几乎要放弃,偏偏那页老照片像是刻意躲在人海中突然探头——正是它救场。

照片却只解开一半谜题。背面的“直宾双市铺”让人挠头星迈网,全国地图硬是找不到此地。调查组干脆南下四川,以“邮局”作突破口查旧邮政簿册,又翻地方志。几番折腾,才确认双市铺即今日宜宾市双石铺,民国初年归“仲权里”辖。地名解密,路线就顺了:“卢定义”这个姓名出现在双石铺户籍薄,于是便有了那天清晨的催喊。
卢定义确认身份后,屋内气氛立刻变得郑重。调查员递上记录本:“老人家,还望您讲讲幺叔的故事。”旧木窗吱呀作响,似在催促时光倒流。卢定义回忆,家里原是盐商兼地主,幺叔聪明好学,1924年偷偷南下报考黄埔,临走只留下一行字:“男儿志在救国。”消息断断续续传回家乡,说他北伐立功,升至团长。再后来,就是战火里的沉寂。

调查组把断片信息拼接:1927年夏,卢德铭任张发奎警卫团团长。南昌起义爆发,他假借调令率部兼程北上,途中收编地方武装,转而投入秋收起义。那支装备精良的警卫团在湖南酃县与毛主席部队会师,成为起义主力。面对是否继续强攻长沙的争议,他一锤定音:“还打?枪炮虽好,可兵力不足,硬拼同归于尽!先转山区喘口气。”这番判断直接推动了“向罗霄山脉进军”的决策。
遗憾的是,部队刚挺进芦溪不久,敌军尾追。9月23日,卢德铭掩护大部撤离时中弹,年仅22岁。几天后,毛主席得报,沉默许久,只说了五个字:“痛失好同志。”乡野很快失去他的消息,随之湮灭的,还有一桩未了婚约——卢德铭早早与颜瑞琴定亲,却始终未能迎娶。卢德铭牺牲后,卢家把三日大的侄儿过继给颜氏夫妇,那便是卢定义。

这些情节,调查员一边记录一边低声互换看法。照片、人证、档案三重印证,卢德铭的形象逐渐立体:黄埔二期学员、北伐功臣、秋收起义总指挥——一位走在二十二岁岁月尽头的大写青年。消息传回北京,张平化立即批示:将照片放大修复,补齐生平文字,列入英烈专题。
1977年10月,井冈山纪念馆重新布展完毕。展厅里,新翻洗的照片静静悬挂。前排右端,青年卢德铭眼神坚定,仿佛下一秒就要跨步向前。展牌下方加了一行今年才确认的资料“家乡:四川省宜宾市双石铺镇”。对照板旁边还附上一句摘录自他致兄长的信:“与其坐看山河破碎,不如提刀马革裹尸。”
炉火旁的卢定义没去参加纪念活动,他更愿在家门口把幺叔的故事讲给晚辈听。“莫小看自己,幺叔只有二十二岁,干的事却能写进书里。”孩子们眼里闪着光。对卢家后人而言,这不只是家族荣耀,也是责任提醒。

多年后,那张修复照片底片已被珍藏进国家二档馆恒温室。研究者检索卢德铭,会看到清晰图像、完整履历,也会读到一个普通乡镇与国家命运意外串联的曲线。至此,“你叔叔是秋收起义总指挥”不再是一记让人发懵的通知,而成为镌刻在档案、记忆和山河里的事实。
翔云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